与黄勉之书 其二
一了百当
原文
【28.1】勉之别去后,家人病益狼狈,贱躯亦咳逆泄泻相仍,曾无间日,人事纷沓未论也。用是《大学》古本曾无下笔处,有辜勤勤之意。然此亦自可徐徐图之。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,未能时时发明,却有可忧耳。来问数条,实亦无暇作答,缔观简末恳恳之诚,又自不容已于言也。
【28.2】 来书云:“以良知之教涵泳之,觉其彻动彻静,彻昼彻夜,彻古彻今,彻生彻死,无非此物。不假纤毫思索,不得纤毫助长,亭亭当当,灵灵明明,触而应,感而通,无所不照,无所不觉,无所不达,千圣同途,万贤合辙。无他如神,此即为神;无他希天,此即为天;无他顺帝,此即为帝。本无不中,本无不公。终日酬酢,不见其有动; 终日闲居,不见其有静。真乾坤之灵体,吾人之妙用也。窃又以为《中庸》‘诚者’之‘明’,即此良知为明;‘诚之者’之‘戒慎恐惧’,即此良知为‘戒慎恐惧’。当与恻隐羞恶一般,俱是良知条件。知戒慎恐惧,知恻隐,知羞恶,通是良知,亦即是‘明’” 云云。
此节论得已甚分晓。知此,则知致知之外无余功矣。知此,则知所谓“建诸天地而不悖,质诸鬼神而无疑,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者,非虚语矣。诚明、戒惧,效验、功夫,本非两义。既知彻动彻静,彻死彻生,无非此物,则诚明戒惧与恻隐羞恶,又安得别有一物为之欤?
【28.3】来书云:“阴阳之气,欣合和畅而生万物。物之有生,皆得此和畅之气。故人之生理,本自和畅,本无不乐。观之鸢飞鱼跃,鸟鸣兽舞,草木欣欣向荣,皆同此乐。但为客气、物欲搅此和畅之气,始有间断不乐。孔子曰‘学而时习之’,便立个无间断功夫,悦则乐之萌矣。朋来则学成,而吾性本体之乐复矣。故曰‘不亦乐乎’。在人虽不我知,吾无一毫愠怒以间断吾性之乐,圣人恐学者乐之有息也,故又言此。所谓‘不怨不尤’,与夫‘乐在其中’,‘不改其乐’,皆是乐无间断否?”云云。
乐是心之本体。仁人之心,以天地万物为一体,欣合和畅,原无间隔。来书谓“人之生理,本自和畅,本无不乐,但为客气、物欲搅此和畅之气,始有间断不乐”是也。时习者,求复此心之本体也。悦则本体渐复矣。朋来则本体之欣合和畅,充周无间。本体之欣合和畅,本来如是,初未尝有所增也。就使无朋来而天下莫我知焉,亦未尝有所减也。来书云“无间断”意思亦是。圣人亦只是至诚无息而已,其功夫只是时习。时习之要,只是谨独。谨独即是致良知。良知即是乐之本体。此节论得大意亦皆是,但不宜便有所执着。
【28.4】来书云“韩昌黎‘博爱之谓仁’一句,看来大段不错,不知宋儒何故非之?以为爱自是情,仁自是性,岂可以爱为仁?愚意则曰:性即未发之情,情即已发之性,仁即未发之爱,爱即已发之仁。 如何唤爱作仁不得?言爱则仁在其中矣。孟子曰:‘恻隐之心,仁也。’周子曰:‘爱曰仁。’昌黎此言,与孟、周之旨无甚差别。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”云云。
博爱之说,本与周子之旨无大相远。樊迟问“仁”,子曰:“爱人。”“爱”字何尝不可谓之“仁”欤?昔儒看古人言语,亦多有因人重轻之病,正是此等处耳。然爱之本体固可谓之仁,但亦有爱得是与不是者,须爱得是方是爱之本体,方可谓之仁。若只知博爱而不论是与不是,亦便有差处。吾尝谓“博”字不若“公”字为尽。大抵训释字义,亦只是得其大概,若其精微奥蕴,在人思而自得,非言语所能喻。后人多有泥文着相,专在字眼上穿求,却是“心从《法华》转”也。
【28.5】来书云:“《大学》云:‘如好好色,如恶恶臭。’ 所谓恶之云者,凡见恶臭,无处不恶,固无妨碍。至于好色,无处不好,则将凡美色之经于目也,亦尽好之乎?《大学》之训,当是借流俗好恶之常情,以喻圣贤好善恶恶之诚耳。抑将好色亦为圣贤之所同,好经于目,虽知其姣,而思则无邪,未尝少累其心体否乎?《诗》云:‘有女如云’,未尝不知其姣也;其姣也,‘匪我思存’,言匪我见存,则思无邪而不累其心体矣。如见轩冕金玉,亦知其为轩冕金玉也,但无歆羡希觊之心,则可矣。如此看,不知通否”云云。
人于寻常好恶,或亦有不真切处,惟是好好色,恶恶臭,则皆是发于真心,自求快足,曾无纤假者。《大学》是就人人好恶真切易见处,指示人以好善恶恶之诚当如是耳,亦只是形容一“诚”字。今若又于好色字上生如许意见,却未免有“执指为月”之病。昔人多有为一字一句所牵蔽,遂致错解圣经者,正是此症候耳,不可不察也。中间云“无处不恶,固无妨碍”,亦便有受病处,更详之。
【28.6】来书云:“有人因薛文清‘过思亦是暴气’之说,乃欲截然不思者。窃以孔子曰:‘吾尝终日不食,终夜不寝以思’亦将谓孔子过而暴其气乎?以愚推之,惟思而外于良知,乃谓之过。若念念在良知上体认,即如孔子终日终夜以思,亦不为过。不外良知,即是‘何思何虑’,尚何过哉”云云。
“过思亦是暴气”,此语说得亦是。若遂欲截然不思,却是因噎而废食者也。来书谓“思而外于良知,乃谓之过,若念念在良知上体认,即终日终夜以思,亦不为过。不外良知,即是何思何虑”,此语甚得鄙意。孔子所谓“吾尝终日不食,终夜不寝以思,无益,不如学也”者,圣人未必然,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学之病以诲人耳。若徒思而不学,安得不谓之“过思”与!
译文
【28.1】勉之你离开之后,我家人的病情日益加重,我自己也是咳嗽腹泻接连相续,几乎日日不停,还有各种事情纷至沓来,那就更不必说。因此,有关《大学》古本的文章迟迟还未下笔,真是有负你至诚恳切之意,不过此事还可以慢慢谋划。但是,我心中对于《大学》古本正文的理解,不能得以时时阐发昌明,这让我深感忧虑。来信问的几个问题,本来确实没有时间回复,不过,看到你在书信末尾所表达的诚恳之意,我又不能不作答。【28.2】你来信说:“依照良知的学问深入体会,感觉到那彻动彻静,彻昼彻夜,彻古彻今,彻生彻死的,无非是这个良知。不假丝毫思索安排,不存丝毫助长之心,自然能够亭亭当当,灵灵明明,神触妙应,感而遂通,没有它不能照见的,没有它不能觉察的,没有它不能通达的,千圣万贤,无不是走在这同一条路上。它不是如神,因为它本身即神;它无须仰慕上天,因为它即是上天;它无须顺从帝则,因为它即是帝则。它本自中正,本自大公。人终日忙忙碌碌,不见它动;人终日无事闲居,也不见它静。这良知真是天地的灵明本体,也是人人皆有的无上妙用啊。我还认为,《中庸》说的‘诚者’的‘明’,即是说良知便是明;‘诚之者’的‘戒慎恐惧’,即是说良知便是戒慎恐惧。它们与恻隐、羞恶一样,都是良知生发出来的结果。能够知戒慎恐惧,知恻隐,知羞恶,这些能知的都是良知,也就是所谓的‘明’。”等等。你在这一段当中讲得已经非常明白。知道这个道理,就明白除了致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功夫可做了;知道这个道理,就会相信“建诸天地而不悖,质诸鬼神而无疑,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这段话,087绝非虚言。诚明与戒惧,效验与功夫,原本就是一个含义。你既然知道彻动彻静,彻死彻生的,无非就是这个良知,那么诚明、戒惧和恻隐、羞恶,又怎么会是别的呢?
【28.3】你来信说:“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,和合融洽、畅达无滞以生化万物。万物之所以有生机,皆得于这个和合畅达之气。所以人心本体的生发之理,天然就是和合畅达的,原本就没有什么不快乐。看那鸢飞鱼跃,鸟鸣兽舞,花草树木欣欣向荣,都是同于此乐。只是由于人的客气、物欲搅乱了这个和畅之气,才导致乐的间断与不乐的出现。孔子说:‘学而时习之’,就是讲了个不间断的学问功夫;‘不亦说乎’的说,就是快乐的萌生之处;‘有朋自远方来’,则说明学问有成,我们心中的本体之乐得以完复,所以说‘不亦乐乎’;‘人不知而不愠’是说,他人虽然不了解我,我却不会让丝毫的愠怒情绪中断我本性之乐,这是因为圣人唯恐为学之人的乐有间断,所以才又如此说。孔子所说的‘不怨天、不尤人’以及‘乐在其中’‘不改其乐’,都是指乐没有间断吧?”等等。乐是心的本体。仁爱之人的心,把天地万物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和合融洽、畅达无滞,万物之间没有任何间隔。你在来信说道:“人心本体的生发之理,天然就是和合畅达的,原本就没有什么不快乐的,只是由于人的客气、物欲搅乱了这个和畅之气,才导致快乐的间断,有了不乐的出现。”这句话讲得很对。所谓的“时习”,就是说要想办法恢复心的本体。“说”,则说明本体渐渐得到了恢复。“朋来”,则心的本体的快乐和畅,充足而没有间断。本体的快乐和畅,原本就是如此,开始时就没有什么可增加的,之后,就算没有朋友来,天下人都不知道我,它也并没有什么可减少的。来信中提到的“无间断”,也是对的。圣人只是做到“至诚无息”而已,他们所下的功夫也只是时时不停地练习。“时习”的关键,在于独处时内心谨慎不苟的“谨独”。谨独就是致良知。良知即是乐之本体。你在这一段所讲的大意都对,但也不应由此而有所执着。
【28.4】你来信说:“韩昌黎(注:韩愈,字退之,世称“韩昌黎”)所说的‘博爱之谓仁’这句话,看起来大体不错,不知道为何宋代儒者认为不对?他们认为爱属于情,仁属于性,所以,怎么能说爱就是仁呢?而我的看法是,性是未发之情,情是已发之性;仁是未发之爱,爱是已发之仁。因而为何不可把爱当作仁呢?提到爱的时候,仁就已经在其中了。孟子说:‘恻隐之心,仁也。’周子说:‘爱曰仁。’昌黎的这个说法,和孟子、周子所讲的并没有什么差别啊。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文人就轻视他的说法吧!”等等。“博爱”的说法,本来就和周子的意思相差不大。樊迟问“仁”,孔子说:“爱人。”所以,“爱”字怎么不可以被称为“仁”呢?过去儒者看待古人的言语,也多有因人而论的问题,你在这里所说的情况正是如此。不过,爱的本体固然可称为“仁”,但还有爱得对与不对之别,只有爱得对,那才是爱的本体,才可以称为“仁”。如果只知道博爱但不论正确与否,也会有不当之处。我曾说,“博”字不如“公”字表达得更彻底。一般来说,解释字义,只能有个大概理解,而精微奥妙之处,必须通过慎思才能领悟,并非能用言语说清。后世很多人,拘泥在文字的表面,专门在字眼上探求,这却正是“心从《法华》转”了。
【28.5】你来信说:“《大学》里讲:‘如好好色,如恶恶臭。’所谓‘恶’,就是说,但凡是难闻的气味,无论何时何处,人们都会厌恶它,这种说法本来也没有什么妨碍。可是,如果说对于美色,任何情况下都会喜欢,那么,难道只要目之所及的美色,都去喜欢吗?《大学》的教导,应当是借世俗好恶的常情,来比喻圣贤好善恶恶的诚意吧。或者说,喜欢美色的心,圣贤之人与普通人是一样的,只是美色过眼,圣贤虽然也知道其美,但是思无邪,就不会有私欲累及心体吧?《诗经》说‘有女如云’,其意为,未必不知道其美;但是,虽然知道其美,却‘匪我思存’,就是说,她们不是我需要惦记的,这就是思无邪,因而心体无累啊。这就好比,看到官位、钱财就在眼前,虽然也知道那是官位、钱财,但却没有羡慕觊觎的想法,如此就可以了。我这样理解,不知道通不通?”等等。人们通常的好恶,或许有不够真切的地方,唯有喜好美色、厌恶恶臭之时,都能做到发于真心,自然要去求个快乐满足,而没有丝毫的虚假。《大学》是就众人的好恶最真切显见之处,告诉人们好善、恶恶的诚心应当如此,这些说法只是用来比喻这个“诚”。现在如果又从“好色”这个字眼上生出这么多的看法来,却未免有“执指为月”之弊。过去的人多有因一字一句所牵制障蔽,从而导致错误解读了圣人经典,正是与此同样的病症啊。对此,你不可不察。来信中说“无论何时何处,人们都会厌恶它,这种说法本来也没有什么妨碍”,这种说法,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,你还需深入反省。
【28.6】你来信说:“有人因薛文清‘过思亦是暴气’(注:大意为,过度思考也是滥用其气)的说法,便想要完全停止思考。如此的话,难道因为孔子说过‘吾尝终日不食,终夜不寝,以思’,就可以说孔子是过思而暴其气了吗?以我愚见推想,唯有外于良知的思考,才能称之为过。如果念念都是在良知上体悟,就如同孔子一样整日整夜地思考,也不为过。不外于良知的思考,就是‘何思何虑’,怎能会是过呢。”等等。
“过思亦是暴气”,这话说得也对。但是,如果因此就想完全停止了思考,那就是因噎废食了。来信说“唯有外于良知的思考,才能称之为过。如果念念都是在良知上体悟,就如同孔子一样整日整夜地思考,也不为过。不外于良知的思考,就是‘何思何虑’”,这些话甚合我意。孔子所说“吾尝终日不食,终夜不寝,以思,无益,不如学也”,孔子未必真是如此,他无非是指出这种徒思而不学之病来教诲人罢了。如果只是思考而不学习,怎能不是“过度思考”呢?
学员心得
蔡同学:
非凡事业,应是社会、国家很需要且有很大难度的事业。两年前,一位朋友曾对我讲:你要使这项目研究、实施成功,不能有一点私心。我虽认同此观点,但当时未学致良知,近来学习后感悟才深刻了。不去除不明、贪欲,就呈现不出良知;没有真切的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,就谈不上成就什么事业!必须诚意学习践行致良知!
高同学:
深悟:听完课,经过老师讲解才明白义中义,才深刻明白起心动念是什么,刚刚明白怎样学习。
笃行:今早晨上班,把科室的更衣室重新布局,为科室人员创造良好的更衣环境。
李同学:
深悟:持续不断地学习圣贤之心,条件成熟时一定有收获。现在的自己已慢慢在体证中。
笃行:昨天接待了做大企业的夫妻俩时,心中淡定了。只要每句话都是真诚地跟对方沟通,就能从容赶走内心的不自信和恐惧的心。昨天真正体证到《致良知是一种伟大的力量》的威力!此本书在家放了4年,自从学习“阳明心学课堂”开始才翻开。
周同学:
反省自己学习阳明心学的起心动念:觉得学了一周了,周日就给自己放个假,起了怠心;有时时间太赶,又着急交作业,就凑合写一句,起了忽心; 一天学习近5个小时,工作又繁忙,身体不适,起了躁心;觉得自己学了阳明心学,比没有学的同学知道的要多,起了傲心;看到别的同学的作业被推荐,起了妒心。
景同学:
今天和小组同仁读了《与黄勉之书》,感觉身心愉悦,特别开心,我是因为读到书中的“乐是心之本体”,就这一句就够我没有不乐的理由,因为心之本体就是乐。还有好多句子比如“人之生理,本自和畅,本无不乐”说的都太好了,太感动了,因为我家先生经常说我“有啥乐的,我就纳闷儿了”,通过今天的学习我才知道原来“乐是心之本体”。
书籍推荐
《致良知是一种伟大的力量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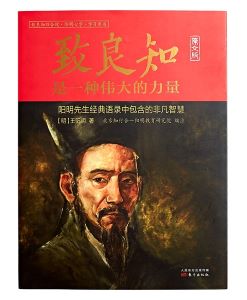
四部曲APP
开发心中宝藏的钥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