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敬教师,敬其宏志
孔子在两千多年之前开创了平民教育,第一次实现了“有教无类”。然而,孔子的一生绝非坦途,他辗转各国之间,忍饥挨饿、受尽讥笑乃至遭受围困,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未得到当权者的赏识,一度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”。但是孔子并未退缩、并未沮丧、并未放弃,原因何在?
《论语·尧曰》载孔子之言:
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也。”
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至高诉求,当你与之连结时,万物将只为你存在,你拥有无穷力量、莫大的价值。当你知道自己为何而生、为何而活,遇到困境时,就永远不会绝望。
“子畏于匡。曰:‘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?天之将丧斯文也,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;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?’”
孔子到了匡这个地方,匡人把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包围起来了,想杀死孔子。为什么呢?
因为孔子的长相跟阳虎很像,阳虎曾经在匡这个地方谋害过匡人,而且以前给阳虎驾车的人,现在是孔子的学生,也在给孔子驾车。
因而孔子与匡人的冲突,不是国与国的战争,而是民间私斗、械斗,这就叫“畏”。
局势非常危急,弟子们都很害怕。
拘之多日,这是孔子一生中惊险的时刻。后来,颜渊赶来了。以下这段对话,几乎是论语中最感人的一个场面。
孔子悲喜交加地说:“吾以汝为死矣。”(我以为你死了)
颜回情深意切地回答:“子在,回何敢死?”(老师尚在人世,我怎敢先死)
短短两句,患难之际、相惜之意、千古悠悠、历久弥新。

然而,冷静下来以后,孔子的心态非常坦然,他说:“文王既没,文不在斯乎?天之将丧斯文也,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;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?”
周文王远去了,他的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?如果上天要让这文化礼制断绝,那么“后死者”——就是“我”,孔子自称——就不可能继承这一文化遗产。如果上天不让文化断绝,要让文化传承下去,那么,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?
《论语·宪问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
“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:‘奚自?’子路曰:‘自孔氏。’曰: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?”
有一次,子路外出回来,到了曲阜城门时,天色已晚,城门已经关闭了,于是子路便在城门口住了一夜。
第二天清晨,负责开启城门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个人睡在了城门口,便走过来查问道:“你是从哪里来的呢?”
子路回答说:“我从孔先生那里来啊。”
守门人笑道:“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,却还是坚持去做的孔丘吗?”
明知做不到,还要做到底。也许,在守门人眼中,孔子是愚蠢的。
其实,孔子的这种“愚蠢”,正体现了他的伟岸。
晨门知道事情之不可为,故不为。相比之下,孔子亦知事之不可为,但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,这些事是“道义”之所在,因而他义不容辞、无所畏惧地奔向自己的命运,“汲汲遑遑,若求亡子于道路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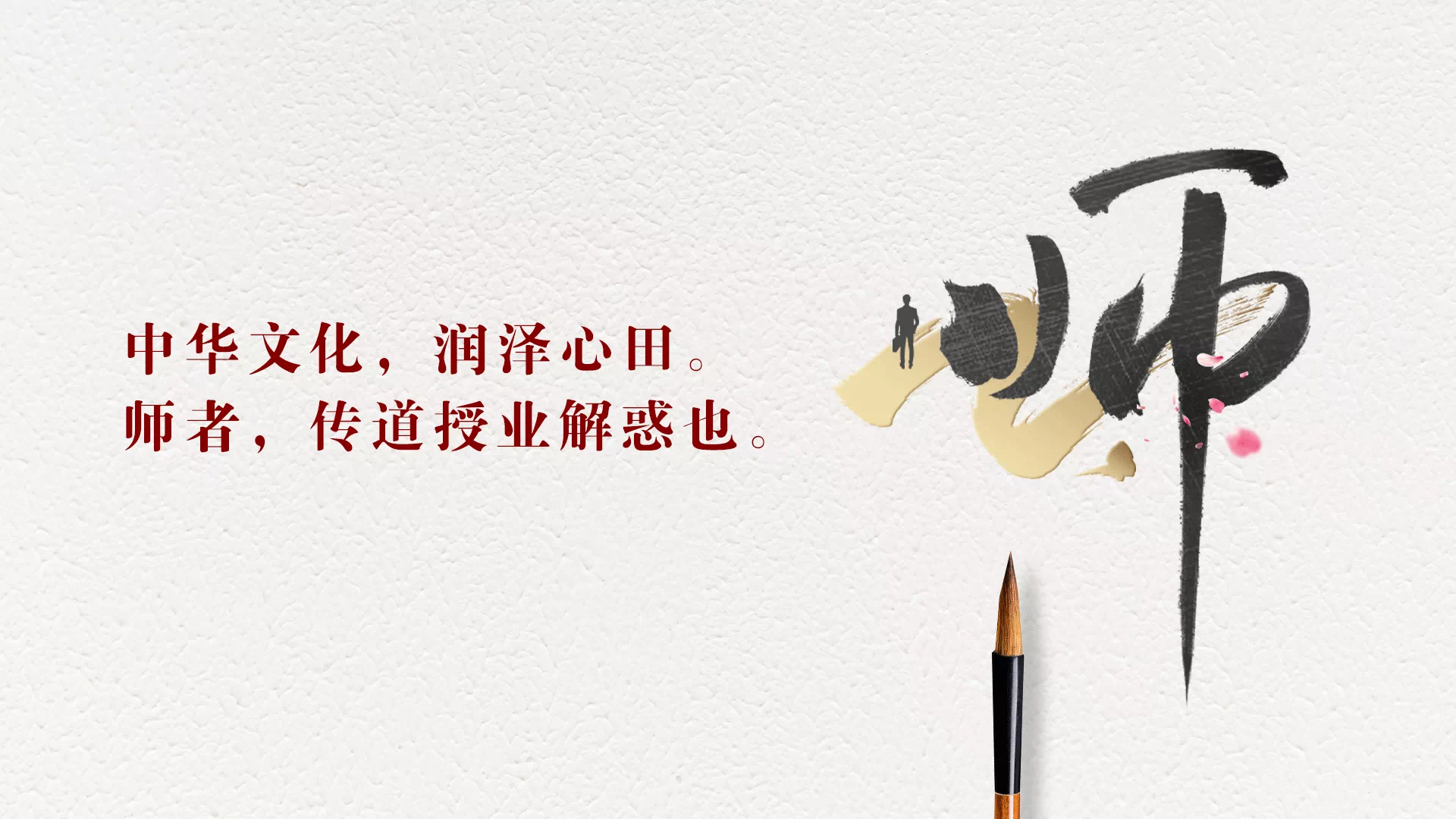
孔子一生,辗转诸侯各国之间,受过围困、挨过饥饿,然而始终得不到诸侯国君的赏识,因而不得其位,但似乎从未见他流露出退缩之意、沮丧之情。
对此,北宋理学家程颐曰:“知命者,知有命而信之也。人不知命,则见害必避,见利必趋,何以为君子?”这一层阐释得更明白,因为君子知道了自己的天命,反而无所畏惧。
近代学者钱穆曾说:“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,正是一种知命之学。”
任何想真正有所成就的人,都是使命驱动,唯有使命,才能赋予其至诚无息的驱动力量。
有了使命驱动,才会为了伟大的目标奋斗,才有用不完的动力,才有永不枯竭的激情。
在全社会普遍重视教育的当下,教师身居其中,是教育改革中极其重要的因素。全社会都应该致敬教师,而广大教师应自觉担当起中华文化的教育使命,托起学生的未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