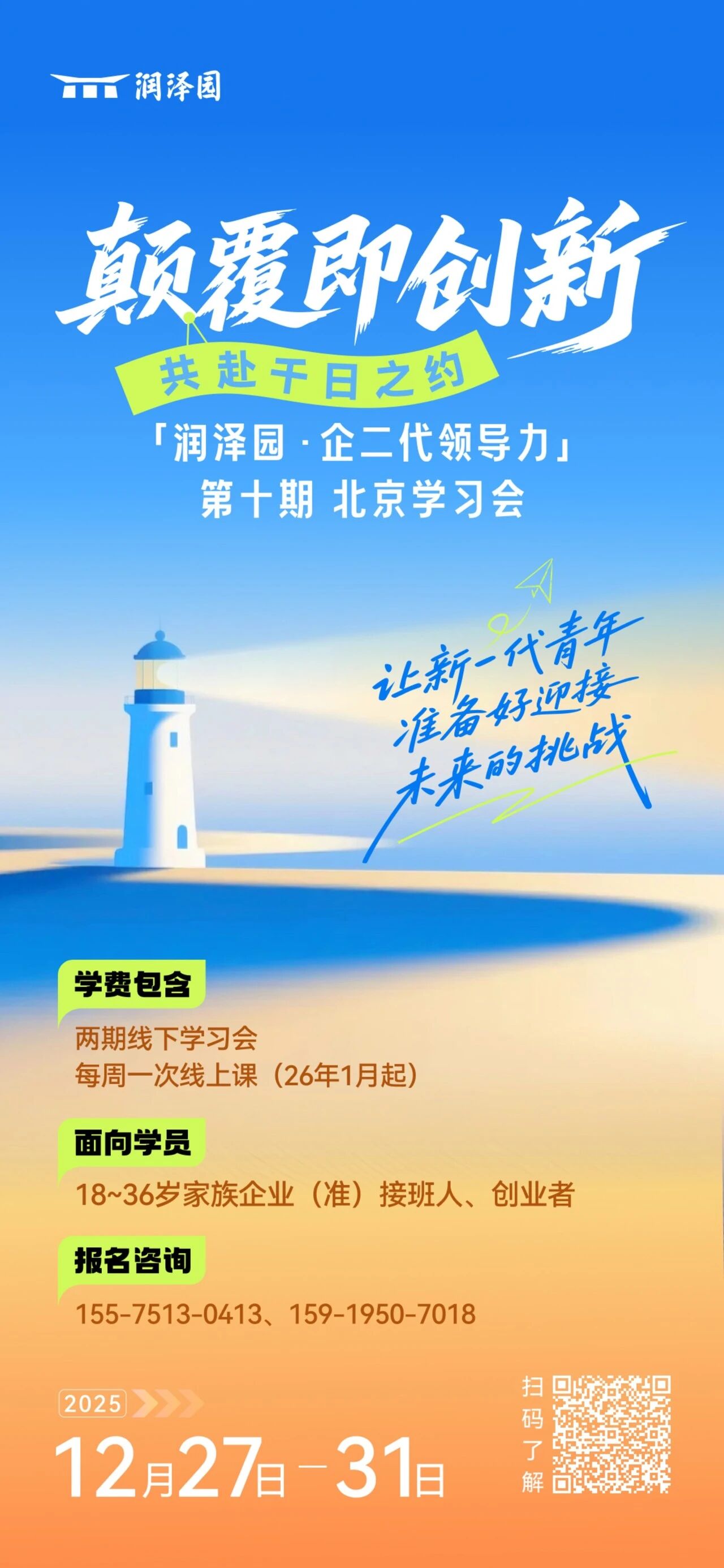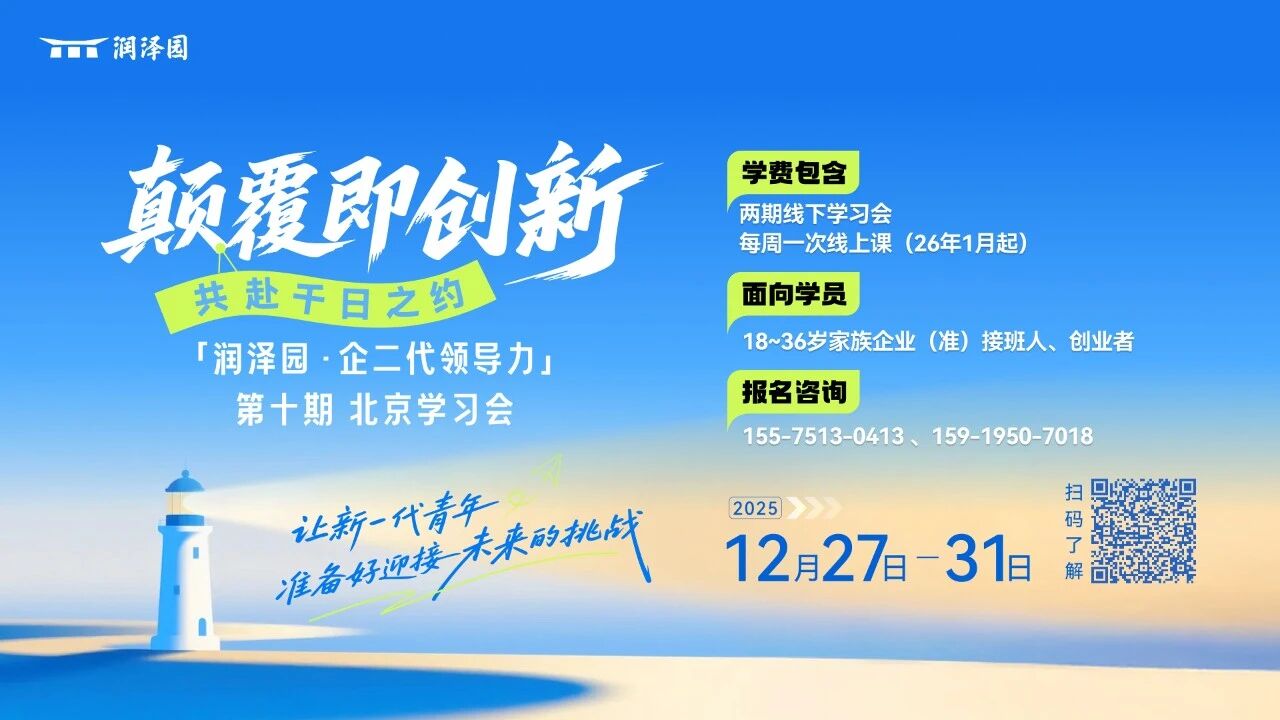“我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企二代”
德鲁克说:“管理是一种实践,其本质不在于知,而在于行。”
对一个青年接班人来说,真正的“行”,不是走进企业,而是先走进自己。
如果不是那一天,他或许永远不会意识到,自己已经背着一个家族走了二十多年。
那是2024年冬天,在南方某沿海城市的一次学习会现场。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提到父亲,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。
“我以为自己在接一个行业的冬天,后来才明白,我其实在接一个家庭的命。”
台下的人静默了。这不像是一个95后说出来的话,更像一个被现实反复碾压过的人,终于鼓起勇气,承认自己恐惧的样子。
而在那之前,外界看到的,只是一个典型的“企二代”:家族在北方某城市从事中国传统手工艺制造,且肩负着非遗传承人的身份。
但很少有人知道,站在光亮后面的这个年轻人,从没真正想过“接班”,却从小被预设了未来的事业走向。
接班对他而言,不是选择,是命题。
道即领导力

人生,仿佛早已被定格
对于29岁的李茂朋来说,他从出生起就背负着家族的使命。
康熙四十二年,李氏先祖因制作花灯手艺卓绝,被御点入宫,负责为皇室节庆盛典制灯。那卷“奉旨入宫,为节庆盛典制灯”的圣旨,现在还珍藏在家中。这份荣耀,成了李家十三代不敢怠慢的命根。
对茂朋而言,这是一种无声的提醒:家族的手艺与担当一代代传下来,不能断。
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份“牵引”,是在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一刻。
高考结束,茂朋曾想去上海——那里有他热爱的文化、设计,还有更广大的世界。但最终,他选择了离家两小时车程的沿海城市,报考了与家业相关的视觉传达专业。“理由很简单,家里做文化工艺,需要设计。”
对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,这算不上选择,更多是一种“不好拒绝的期待”。
“因为离家近,周末可以回来帮忙。”这是家里给出的理由,也几乎是命令。
茂朋说:“其实当时我第一次感到——人生不是我自己选的,但我也没反抗。”
原因也简单——作为儿子、作为长孙,不反抗才是“乖”的表现。
于是,他顺着这条轨道毕业、回家、进入工厂、跟着父辈做项目、招投标……
他以为自己会按照既定路线走完这一生。
直到疫情出现。
2019年毕业,2020年疫情。茂朋刚从校园迈向社会,就被现实按在地上。
那一年,他们在北方某城市的文化项目通过验收,几百盏灯亮起未及二十天,便接到了封停的通知。
更残酷的是随后三年——项目停摆、执行中断、资金卡在中间、工厂堆满了货、工人们等着工资。
茂朋第一次真切地看到“老一代创业者的痛”。
父亲一天到晚站在库房前,看着那些亮不起的灯,看着做了一年的货堆满仓库,看着在厂房里等待的工人们……
那天风很大,父亲站在库房门口,说了一句:“我不扛,谁扛?”他清楚地看到父亲眼底有泪光闪过。那一刻,“接班”在他心里不再是继承,而是承担责任。
可越是明白,他内心越痛。因为那时,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。
疫情后,城市的文化活动大幅缩减,预算下降,项目量断崖式滑落。
一个行业往往不是被竞争打败,而是被时代悄然抛下。面对残酷现实,他开始动摇:“这个行业还有未来吗?而我,又将走向哪里?”
一边是父辈的坚守,一边是行业的动荡,而中间那个被家庭牵引着前行的年轻人,却在摇摆与迷失中寻找出口。

李氏花灯传承人 李茂朋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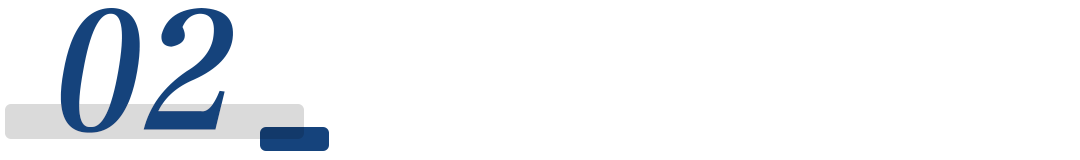
“你永远是个孩子”
2023年,茂朋去听了一堂课。他以为就是听听,没想到那堂课让他第一次看见自己——也看见这些年跟着家庭往前走时,心里藏着的那口气。
“这口气,从小就有。家里说你是长孙,要接班;说学设计,对家里有用;说毕业了去公司,是应该的。我都照做了。”
直到行业变了,父亲艰难地撑着企业,他才明白:自己这样走下去,不是接班,是迷失。
那堂课像是把心掸了一遍灰,他第一次敢承认:自己从来没有想过“想不想干”,只是一直觉得“应该干”。
那晚,他坐在父亲对面。话说出口时,嗓子干得发疼:“爸,我不想干(接班)。”
父亲愣了一下,什么也没说。
沉默里,他仿佛能感到父亲的难处——或许,父亲也不知道路在哪里。
想到这里,他心里一紧,“父亲最怕的,是祖辈苦苦撑下来的这点东西,会在自己手上散掉。”
但对茂朋而言,真正的压力不是“接班”,而是“你永远是个孩子”。
几乎所有青年接班人,都经历过相同的困惑:你再努力、再聪明、再能干,在父辈眼里,你依然是那个从小跟在他们后面跑的孩子。
茂朋说:“我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墙。你说你的想法,他们会听,但他们不会相信。”
“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,而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不确定性,他们的价值体系,是在市场中实战出来的。不是观念问题,是时代的问题。”
上一代创业者,靠的是直觉、经验、人脉。而年轻人的路径相反:洞察、战略、逻辑、复盘。
当这两套系统在同一个会议桌上相遇时,冲突是必然的。
对父辈来说,“我知道怎么干”;
对茂朋来说,“世界已经变了”。
但这些话,他不能说。因为他说出口的每一句,都像在推翻父辈的过去。
这或许是企二代最难的地方:要在“尊重历史”和“建立未来”之间找到一条路。

“青年人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胜利”
2023年,茂朋参加了人生第一场学习会,是针对青年接班人的课程。
他说第一天就懵了,被“照见自己”这件事震住了。
他感慨:“原来我一直在帮父辈扛,可我没扛过自己。”
他开始认真思考几个从未问过的问题: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?我为什么这么累?我是在为家里工作,还是替家里活?我是为了父亲的事业继续下去吗?还是为了证明自己?
这些问题,父辈不会问,但年轻人必须回答。
于是他连续三次学习,每一次都像把自己的内心翻看一遍:
第一次,他意识到自己是在“被推着走”;
第二次,他发现父亲也很脆弱;
第三次,他说自己必须成为一个能被父辈看见的人,而不是一个执行者。
在一次学习会上,有同学问老师:“我到底是该出去闯,还是该留在家族企业?”
老师回答:“青年人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胜利。”
“那一刻,我像被敲醒。我终于明白:父亲不是不信任我,而是我目前没有能让父亲心服口服的‘胜利’。”
“在父亲眼里,我永远是孩子。我说的所有战略,他们听不进去。不是因为他们顽固,是因为我没有证明自己。”
茂朋告诉自己:如果我想接班,就必须先离开;如果我想改变家族,就必须先改变自己;如果我想让父亲听我的,就必须先赢一场。
外界以为的企二代:家里有资产、有资源。但真正站在接班节点的人看来,这些都是压力:“既然你生在这儿,你就没有失败的权力。”
茂朋坦言:“别人也许可以‘重启’,可以换赛道,但我们不行。我们输不起。”
外界以为是金汤匙,只有他自己知道,是一块沉重的家族基石。过去在长辈手里,如今落在他这代人的肩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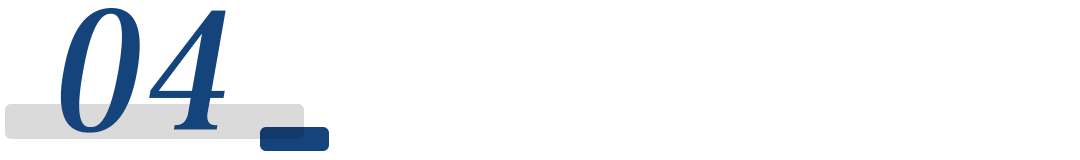
“我学会了先向内走,再向外走”
2024年,茂朋做了一个关键决定:先创业,再接班。
“我不是不要家族,也不是不认父辈的路。我只是要先走一段我自己的路。这样回去的时候,我才不是那个孩子。”
他想清楚了三件事:能力不等于话语权,胜利才等于话语权;要改变家族企业,必须先在外面试过、打过、赢过;自己在外面经历的所有艰难,未来都会成为接班时的底气。
他要做的不是“摆脱家业”,而是带着自己的世界回来,让家族企业拥有新的可能。
真正让他转变的,是“使命感的崛起”。
有一天,他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我未来做的事情,要能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光。”
这不是口号,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力量。
于是,非遗不再是手艺、项目、订单、招投标。在他心里,它们变成了一种“文化科技产品”,变成可以走向国际的IP,变成未来可以跟世界对话的文化内容。
茂朋说:“非遗不是守过去,而是要活在现在、走向未来。”
这是一个年轻人第一次进行“战略思考”:如今,线下文旅需求存在;但传统彩灯项目受政策、预算、季节等因素影响大;市场正在重构;传统工艺靠旧打法已经无法支撑未来的增长。
当一些企业选择等待“春天”时,他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方向:“非遗手艺的价值不应该只存在于节庆,它需要进入现代商业体系。”
他第一次跳出“做项目”的框架,开始讨论“产品化”,思考如何让非遗拥有更稳定、更规模化的商业路径。
他给自己立下三个方向:非遗的现代审美化(让产品更年轻);工艺的工业化结合(让生产更稳定);文化内容的IP化(让故事成为资产)。
“文化不是装饰,是生意。生意不是对手艺的消解,而是它走向未来的唯一通道。”
“我不只要做一个好儿子,更要成为父辈的同行者。”
经过学习,他发现:“我和父亲,并不是站在对立面,我们只是站在不同时代里。”
对这一点的理解,让他从心底松下来。
“我以前总觉得父亲‘不懂我’,现在才知道,他在他那个年代,也曾是我这样的年轻人。我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坚持、为什么谨慎、为什么不敢放手。因为父亲属于‘做工厂起家’的一代,每一分钱都是真金白银挣来的,没有资本红利,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超车机会。他们习惯了靠手做,而不是靠市场逻辑。而我,是携着新时代的视野、资源和教育成长起来的。”
两代人之间没有对错,只有时代的落差。
“父辈习惯了‘冲在前面’,但年纪越大,越希望有人能接过方向盘。只是这件事,他们从来没说出口。”
“我现在明白了,父亲不是怕我做错,他是怕有一天我不在他身边。”
想明白了这些,茂朋对“接班”,有了新的理解:“成为一个能独立判断、能承担责任、能真正为企业负责的人。”
他现在做的事,是在文化内容与现代商业之间,找一条“新生路径”:把传统非遗的技艺,转化成更具有现代设计语言的产品;让工艺与科技结合,提高复购率,而不是只靠季节性项目;让品牌成为资产,而不是依赖人脉和关系的“一锤子买卖”。
这条路很难,甚至比接班还难。
茂朋说:“我学会了先向内走,再向外走。我需要一场胜利。不是为了证明父辈错了,而是为了让父辈放心。”

李氏花灯“哪吒出海 共赢未来”亮相第21届文博会
结 语
成长,是一次心的重建。
这位95后,曾经最大的卡点是:想证明自己,却不敢真正面对自己的恐惧。而现在,他愿意照见内心,也愿意承接未来。
如茂朋所说,“接班,不是把父辈的路继续走下去,而是把我们这一代的路开出来。如果我们能让传统工艺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,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”
每一代年轻人,都要在时代里完成自己的攀爬。
他正在做的,不是复制父辈,而是成为那个能带领企业穿过下一个时代的人。
也许未来的路更陡峭、更多风雨、更多未知,但他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:他终于选择自己站上舞台。并且,他准备好了。
这位95后,已不是一个背负命运的孩子,而是一个能带着使命往前走的成年人。